 发布时间:2025-08-22
发布时间:2025-08-22
 浏览量:247次
浏览量:247次

踏进看守所会见室,指尖触到那冰凉的铁栅栏,当事人眼神里的复杂情绪迎面扑来——是绝望、焦虑,还掺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。这一刻,法律文书上那个冰冷的“犯罪嫌疑人”符号,突然具象化为一个活生生的人。

“你是律师?为什么要替这种人辩护?”这质疑几乎成了职业背景音。亲友不解,公众侧目,甚至我自己也曾面对镜中倒影,叩问内心。刑辩律师,何以在道德审判的风暴眼中坚持己见?
程序正义,正是我们坚固的守护对象。
法庭上,我们并非为罪行开脱,而是以法律为刃,守护程序正义。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示: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,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。”被告席上的身影,在判决生效前,仅仅是一个法律标签下的“嫌疑人”或“被告人”。我们为之辩护的,正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,是程序正义不被扭曲的底线尊严。

我见过太多“眼见未必为实”的案例。多年前一桩凶杀案,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,现场目击者言之凿凿。我们顶着巨大压力,反复核查案卷中一份不起眼的通话记录细节,终确认案发时他根本不在现场。当法庭宣布无罪释放,他母亲颤抖着跪倒在地时,程序正义的冰冷条文瞬间有了滚烫的生命温度。
“坏人”的权利,恰是好人安全的基石。
有人诘问:“若他真犯了罪,辩护岂非助纣为虐?”此问暗藏危险逻辑。若律师仅凭内心预判决定是否辩护,法律的天平将倾斜于个人好恶。今日你因“坏人”标签剥夺其辩护权,明日你亦可能被贴上标签而孤立无援。法治的要义,恰恰在于以规则之刚性对抗人性之偏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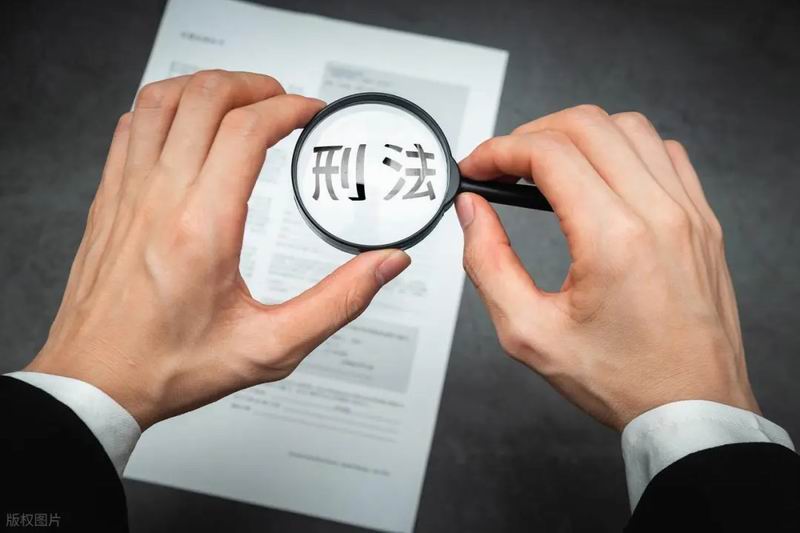
刑辩律师,是法治精密仪器的校准者。我们质证每一份证据,审视每一个程序环节,推动控辩双方在对抗中逼近真相。如同匠人打磨玉石,磨去的不是核心价值,而是遮蔽真相的杂质与程序瑕疵。这过程或许使控方工作更艰巨,却让终结论更经得起历史拷问。
我们守护的,从来不只是某个人。
每一次有力的质证,每一次严谨的程序监督,都在加固司法公信力的基石。当公众看到即使“罪大恶极”者也享有法律赋予的辩护权,当“疑罪从无”原则在个案中被坚定践行,法治的信仰才能在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。
走出看守所,夕阳在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光芒。手铐撞击的冰冷声响仍在耳畔,但心中信念如阳光般清晰坚定——我们守护的,从来不只是某个人。
我们守护的,是程序正义这束穿透偏见的光,是法律天平上不容倾斜的砝码,是让每个人在司法面前保有尊严的底线。这守护或许孤独,却正是法治大厦得以矗立的深层根基。
刑辩律师,注定是戴着荆棘王冠的守望者。但正是无数微光的汇聚,才足以照亮通往正义的幽深隧道。
本文作者
